谈诗|辛波斯卡:关于“大问题”的“小回答”
2016/6/11 三联生活周刊
点击上方“三联生活周刊”可以快速订阅,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在一颗小星星下》
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
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请别生气,幸福,如果我将你据为己有。
死者,但愿你容忍这一切,我的记忆正在枯萎。
每一秒钟我都忽视了整个世界,于是,我向时间道歉。
我为将新欢当成初恋向旧爱道歉。
原谅我,远方的战争,原谅我将鲜花带回家。
原谅我,外露的伤口,原谅我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我为小步舞曲唱片而向在深渊里呼喊的人道歉。
今天,清晨五点我仍在熟睡,为此我向等候在火车站的人道歉。
宽恕我,被追逐的希望,宽恕我一再地大笑。
宽恕我,沙漠,宽恕我未能及时带来一匙清水。
还有你,猎鹰,这些年你依然如故,在同一个笼子,
在空中,你的目光凝固在一处,
原谅我,即使你已变成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条腿而向被砍倒的树木道歉。
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
真理,请不要太在意我。
尊严,请对我大度些。
容忍我,哦,神秘的存在,容忍我拆掉了你裙摆上偶然的针线。
灵魂,请别指责我偶尔才拥有你。
我向万物道歉,我不能同时到达每一个地方。
我向所有人道歉,我无法成为每一个男人和女人。
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就不能变得公正,
因为,我是我自己的障碍。
言语,不要怪罪我借用了庄严的词句,
又竭尽全力让它们变得轻盈。
(胡桑译)
这首辛波斯卡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诗,在反映辛波斯卡的诗歌特点上,也可称代表。就像波兰诗人尤利扬·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确是微小事物的观察者与表现者。那些“大的背景”,或许因为她早年并不满意的诗歌经验而在之后的写作中有意识地隐去,但更重要的是她天性如此。而对那些微小的事物,她用并不习以为常的眼睛,在足够近的距离下看到它们的变形,进而写出我们没有看到的隐秘。

辛波斯卡对经验的提炼直接清晰,反映在她的语言上,就有一种白描式的简洁和俏皮,它不沉重,但是纷繁。在诗中,她把抽象的概念诸如偶然、必然、幸福、希望、真理、尊严、灵魂,与那些具象的事物并置,新欢旧爱、战争与鲜花、猎鹰的标本,四只脚的桌子。诗人用自己的想象把不同场景与事物关联起来:因为鲜花而想到远方的战争,因为小步舞曲而想到深渊里呼喊的人们,因为清晨的熟睡而想到火车站的等候。截然不同的经验与时空在诗句中被“创造”出了关联,它们也构成了前半部分诗歌的主体,一个交织着真实与想象、此刻与彼时、抽象与具体的世界。这种写诗的方法在辛波斯卡的诗中并不少见,比如那首更著名的《种种可能》:“我偏爱电影。/我偏爱猫。/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我偏爱狄更斯胜过杜斯妥也夫斯基。/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欢/胜过我对人类的爱。 /我偏爱在手边摆放针线,以备不时之需。/我偏爱绿色。/我偏爱不抱持把一切/都归咎於理性的想法。/我偏爱例外。/我偏爱及早离去……”

然而,这些经由诗人主观意志而并置的事物与情境,真的彼此相关吗?我们听到诗人在诗中不断地说“原谅我”、“宽恕我”,为一种境况而向另一种境况“道歉”,这种道歉在现实里显然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之间并无因果,也无联系。就算辛波斯卡在这些充满矛盾的事物中发现了蕴藏在它们当中的痛苦与荒谬,最终它也只是存在于诗句之中,似乎于事无补。词句无论如何凝重和庄严,最终还是被变得“轻盈”。诗人最后向万物道歉,向出现或者没出现在诗句中的一切道歉——“我是我自己的障碍”。这个“我”,可以是诗人,是诗本身,也可以是诗人为之致歉的一切。诗人的道歉也和这首诗歌本身一样,看似庄重,但又轻盈;看似简洁直接,却又纠结缠绕。词语里闪烁着洞察的智慧,但又清楚它本身无法穿透经验和现实的屏障。
对这种限制与障碍的表达,是辛波斯卡迷人的地方。我们仿佛能看到诗人身处诗歌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两难。写诗这种行为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矛盾与冲突:全部的经验为诗人提供了这种可能,但是这些经验和文字之间又有一道无法突破的壁障,你不能通过完成一首诗,来获得主体行动的力量和真实世界的改变。

但这绝不是说诗人缺乏对诗歌的信仰。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冲突之中的立场更有说服力。在诺贝尔获奖词中,辛波斯卡谈到诗人作为一个职业的合理性,也谈到自己写作的灵感。她并不把灵感归为诗人或艺术家的特权,而是属于“那些自觉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以爱与想象去完成工作的人”,诗人则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选民:“无论灵感是什么,它总是诞生于持续的‘我不知道’。……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在努力回答这句话,但当稿纸被打上最后一个句点时,诗人就变得犹豫,开始领悟到,这个看似别致的答案纯粹是权宜之计,绝对不充分。”所以对辛波斯卡来讲,并不是通过写诗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不断寻找“我不知道”背后的秘密,用以反抗“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的日常,从而发现“令人惊异”的世界——或者说,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令人惊异’是一个隐藏着逻辑陷阱的描述语。毕竟,令我们惊异的事物偏离了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准则,偏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显见事物。但关键是,并不存在一个显见的世界。我们的惊异独自存在,并不以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为基础。”诗歌中被清晰赋形的每一个词语,都要经过拷问,都被权衡,再重新建立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虽然是“大问题”的“小回答”,但终究是一种在审慎的智慧与问询中建立起来的回答。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诗歌与现实经验之间这种缠绕而又分离的关系,辛波斯卡把她精心打磨的诗歌推向读者,而让自己的生活隐匿其后。她并不会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写进诗中或者展露人前,但是她的诗歌却从探索个体境遇起步。她的同胞诗人米沃什评价她是一名“知觉诗人”,“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辛波斯卡当然“无法成为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但这些大问题的小回答却可以属于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假如他们也“偏爱写诗的荒谬”,也相信没有一个存在是寻常的。
(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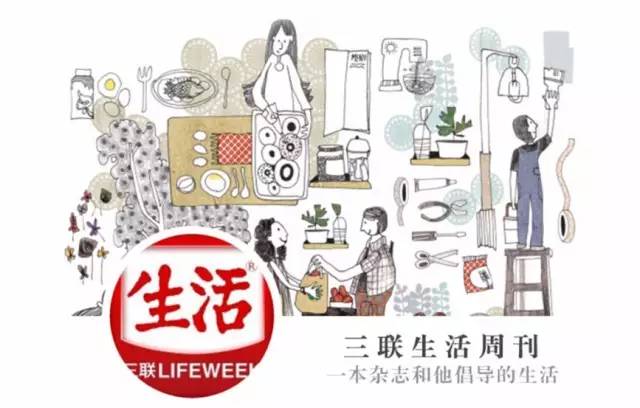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三联生活周刊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