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音乐是为了献给离去的人
2016/7/21 三联生活周刊

王健
“你看过《天亮时请将悲伤终结》这部电影么?”我问王健。
“当然看过,”他转向台下的观众说,“这是一部讲述古大提琴音乐家的非常棒的电影。”
“科隆布和马雷,两位法国古大提琴家,科隆布隐居森林里面拉琴和钻研琴艺,马雷是风光的名利双收的宫廷乐长,您觉得哪一位......”
我还没有说完,王健接过话题,好像一时记不太清楚,很快了结了这个话题。
我忍不住追问:“可是历史选择的是马雷。”

电影《天亮时请将悲伤终结》剧照
这是在上海大剧院的一个大师见面会活动,我被找去向他提问。
在我心目中,王健就像那一位隐居在森林里面独自拉琴的科隆布,他正好有个同时代最强大的对手,马友友。一位热情洋溢,一位深情质朴,构成对照。王健比马友友小十三岁,这个年龄差很不幸,若是两人相差二、三十岁,大概就没有竞争了,但两人几乎同辈,王健出道的时候老马正如日中天,在美国发展的华人大提琴家里面,人们几乎只认识马友友。
王健内向,几乎不太愿意搞宣传,貌似更难打开事业局面。而我却觉得,正是他的个性挽救了他,让他和马友友呈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面貌。在人们的印象里,马友友适合搞派对带领众人一起玩音乐,而王健是孤独拉琴的人,因纯粹、投入而略带感伤,似乎离音乐更近一些。真正的乐迷,貌似更青睐他。

会不会是马友友的热情洋溢,让他不自觉走向了对手的反面?我觉得并不是。如果你听过王健小时候拉琴,还有他拉琴的模样,会发现有一些难以言传的情感藏在他的性格最深处。人们都记得斯特恩那部获奥斯卡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王健真是幸运的人,他在里面有大量镜头,并且在片尾的长长字幕中独奏。看完之后,大家都记住了这位中国的莫扎特。这也弄得他如今再努力都难以赶上童年的风光。在电影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笑起来眼睛弯弯,没心没肺。拉琴的时候,他好像被音乐莫名震慑住了,浑然肃穆的模样。摄影师对他架起家伙,开大灯拍他,他也毫不所动,不害怕,不停歇,按照自己的节奏拉下去拉下去。犹记得的有一段,男孩脸上无助又隐忍的神情,那是我们熟悉的童年时代的无力感:初次离开亲人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的第一天,天空阴沉沉的,雨下个不停。
我问他,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小时候学琴记忆深刻的事情。他说基本不记得了。他大概是晚熟的人,不急不缓,慢世界一拍,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时代如何变化,别人追逐什么,都不太会影响他。他有音乐。音乐如大海,一头扎入其中,便是沉浸一生。
王健大概并不认为自己像电影中的圣塔科伦布,如今中年的他,中国文人气质浓郁,讲话是温柔细密的上海风格,还喜欢各种呆萌宠物,说到音乐是献给离开的人的时候,忽然间眼里闪着泪光,但他马上离开了这种情绪。他比科隆布谦逊儒雅,也更理性。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性格、经历、环境交融的产物。可是工作结束,一下台来,他又变回9岁时简单可爱的样子。我顿时想到他的演奏,他可以直接把音乐变作情感的流动,这对他来说非常简单,普通乐手修炼毕生的境界,他好像本来就在那里。

这是他在上海演奏之前的预热活动。
这一次,他回家乡演奏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最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也曾是他第一次在美国登台表演的乐曲。
犹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台看到王健拉琴,正是这首《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他是有魔力的,你一旦听见他就不想换台了,一直跟着听完。这是杜普蕾的代表作,想突破她的演奏几乎不可能。他要如何摆脱她的影响呢?只见他浑然沉浸在音乐中,似乎没有做出主观的情感表达,他在这片神秘的海洋里寻找,对那种神秘充满敬畏,因此谦逊而迷惘。他不像杜普蕾那样执拗地哀伤,他的悲伤无限婉转。我想起他小时候拉琴的脸,懵懂,却又好像什么都懂。但他在这首乐曲中寻找什么呢,音乐中为什么会有无言的隐晦?我想起聂鲁达说,这个问题可以去问黑夜。
后来我去听他现场演奏,发现这首乐曲的诠释已经完全不同了,倒并非刻意为之,是因为人生走到了一片自由开阔的天地。第一乐章的深情旋律,被他拧成了一条长长的线索,气韵起伏,却毫不松懈,几乎是用一种中国的太极招式,把听者牢牢束缚,无法呼吸。中间的快板,他用一种颤音一般的弓法演奏细密的节奏,就是把快板的音符线条化了,也让人想起中国音乐,譬如江南丝竹的花式变奏;最后一个乐章非常奔放,力量与热情源源不绝。听完之后,我和朋友们站起来大声鼓掌,音乐值得赞赏,更值得庆祝的是,人到中年他依旧感情用事。

在掌声里,他回来谢幕,并坐下来又拉了两首巴赫。
十多年前,王健就录过一张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专辑。那是最能够完整展示他的乐曲。王健一直都是直接简单的,毫无掩饰。他细诉,他多虑,在亲密的叙述中,情感蜿蜒曲折,沁人心脾,音乐中有一种非常婉转细腻的古典情意,你也总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演奏西方音乐,他深谙妥贴的艺术。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小piece中,他是很不甘平庸的,他用弱音,用流转的节奏,倏忽避开了烂熟的方式,如此四两拨千斤,但毫无游戏感。
他后来加演的那首巴赫,就是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里面最动人的那一首,第二首中的“萨拉班德”。他越拉越慢,几乎不在意声部中那些隐伏线索,也不打算奏得悲伤动人以取悦听众,也不想陶醉其中。旋律几乎是凄凉的、苍白的、思省的,硬是把巴赫拉出了《二泉映月》的意思。他并不打算追求完美,似乎近来练琴都不太用功,有错音也有走音。这是真看开了啊,我想起他总是说,只为自己拉琴。
他还说,音乐是为了献给那些离去的人。

再次让我想起《日出时请将悲伤终结》里面那位隐居的古大提琴家,圣塔科隆布,他沉默固执,外冷内热,表达情感的方式严厉而执拗。当然王健是不同的,他更柔和细致,如今,他的演奏更丰富更有激情,也更坦然开阔了。
在那些古老的传说里面,人们把深情赋予音乐家。大概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人们觉得音乐家最懂感情,于是在他们身上投射一个美好的愿望。科隆布深爱着死去的妻子,每天拉琴只为沟通鬼神,为了让妻子重现。他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古希腊的版本。在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位最天才的音乐家奥菲欧,他的琴声与歌唱让海妖塞壬都甘拜下风,后来他深爱的妻子尤丽迪西去世,他抱着琴追到冥府,以琴声打动冥后,带回爱人,可是不小心一个回头的差错,又让他永远失去了爱人。在这些故事里面,人们用不幸与悲伤成全了他们的深情。
而现实中的音乐家,或许他们的深情无人能负担,只能呈现在音乐中,音乐夺走了他们全部爱恋,手中的乐器从小伴随,也是爱恨交集。他们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世俗情爱不过是为体验人生,深入音乐。表达世上的深情才是他们的使命。
电影中的马雷后来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古大提琴家,被载入史册供后世膜拜。但尽管如此,古大提琴仍旧跟随时代消失了。而圣塔科隆布这样的音乐家,并不在意身后留名,他遁隐而去,只留一个背影,变成一个传说。

电影《天亮时请将悲伤终结》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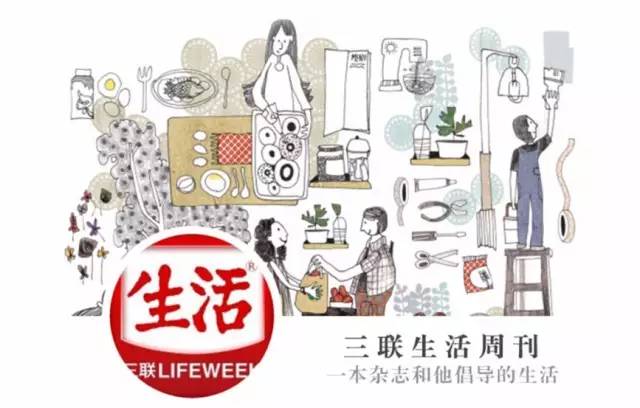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三联生活周刊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