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案:我们欠读者一个真实的高承勇
2016/9/12 三联生活周刊
在白银那几天,我时常睡不好,这座城市有种封闭而无聊的基调,不知是否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高承勇案那么一渲染,每个来客都不禁在主观意念上为它蒙上一种萧条气。所以每一天,在无法接近他的核心家属之际,我心里像压着块石头,一方面是在新闻报道中最麻烦的主体缺位,另一方面是潮水般的网络信息将你冲刷到六神无主。我和同事老刘前后脚去到白银,当时分好工是我操作事件本身,而他负责一篇分析,关于犯罪心理学。第二天,我越来越打退堂鼓,甚至想跟他说我不写了,就当来打个酱油。显然,我感到他的犯罪心理学更接近如此杀人的本质。

高承勇被抓时的小卖店
我当然也尝试着去找他的妻子,那个按照目前推断,不知跟“恶魔”同眠了28年的农村女人,这辈子没有干过工作。但是预料中,无论是高的老家青城镇,还是他们在白银的邻居,即使愿意告诉你对于高的印象,但谁会指导你如何去找到一个如今背负着最重的耻辱柱、而又手无寸铁的女人?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我只知道,最近她再没有在青城出现过,虽然那个家也是她的,她嫁过来后住了14年。有一个高家族弟跟我说,“找不到!警察都在找他呢。”

犯罪嫌疑人高承勇(中)被抓捕现场
白银这件事,我们要探寻的无非是两条线索,其一就是高承勇为什么要在14年间残忍杀害十一人(也许还不止);其二就是,是什么外因使得白银在14年间能够“容忍”一个杀手那么潇洒自如地,用几乎同种手段取走9条性命?后者是容易构建的,从这座城市的起源、人员构成、行政结构、甚至公安数量……前者的话却是致命要害,首先你无法跟这个人对话,我们跟凑集在白银的一些同行聊,我还玩笑说,随便想想就是到了最终时刻,央视去做一个对话……
确实,警察可以给出的也不多,在审讯的初期,的确有知情人爆料些细枝末节,比如第一桩案子的初衷是盗窃,慢慢趋于劲爆的是他见血就满足、喜欢在奸尸同时取人器官、甚至诸如把器官装袋带到黄河边扔掉……不过,那么血腥的细节,当我再次去找那位对媒体作此口述的郝局长,他却说“这我不知道,不是我说的”。几乎所有矛盾冲突显著的社会事件,都会多少陷入一种罗生门,有时我们无法究其所以然,甚至应该接受罗生门本身就是一种真相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我对老刘说,哪怕见他的妻子张清凤一面,知悉她目前的状况,就算她不肯开口,也许都算我们进阶。

高承勇老家所在的青城镇城河村
在青城采访的时候,其实也头疼,没有人可以还原他真实的打工路径,也就无法客观地联系并阐述他之于青城与白银间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下杀人的大环境。高氏在青城是个望族,他们多沉湎于本宗的历代才子豪杰,无法解释这座耕读传家的几百年城镇怎么会出这样一个人,于世族长高孝文愤慨又痛心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况高承勇家也不赖,爷爷在民国时开中医馆子,是镇上的能人,高承勇这一辈就五个大学生,只是后来家道中落,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穷”。

高氏祠堂一直是青城古镇上的著名景点
族人把他杀人的原因描摹地煞有介事,“他为什么杀人呢?一个是因为交过一个女朋友,没谈成受了刺激,另个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见到高孝文的时候是在一个镇上的农家乐里,一个跟他一起喝酒的资深族人这样对我说。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之前交女朋友受了刺激?”“这个报纸上有。”确实,当我们时常与老乡在聊到兴致盎然处,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的,他们多半是回答报纸上有,或者央视说的......不论你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新闻记者,作为闯入者来说有一种困境,那就是人们当察觉自己在被研究、被质疑和被观察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不会交付最本真的自我的。
其实,我对高承勇的人生受过些什么挫折已经了无兴趣,无非就是读书恋爱不顺、抑或家里太穷,正如他的一位初中同班女同学大叹口气说:“哎呀,那个时候谁不穷啊?”,高的人生不算最坏,这座对学问和仕途有浓重情结的古镇在七八十年代就极重视高考,那是走出农门的唯一方式,很多学子别无选择,所以落榜了复读几年都不在话下。高承勇即使没有考上大学,但相比那些被挤下独木桥,终身务大棚的同辈,他好歹是“出去”了。

高承勇初次作案地点。永丰街小区正在改造中,原来的平房早已拆掉
当一个人的初衷是盗窃,但最终杀了人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将贫穷放置在主要驱动力的位置上;但当一个人在杀十一条人命,并间而伴有盗窃痕迹时,你绝对不能用贫穷或挫折去解释最根源的动机,这是我即使写了洋洋万字稿,总觉一拳打在棉花上,无法穷尽这个人的原因所在。我甚至觉得我们很僭越,所以对同事老刘说,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交给科学。

非常有80年代感觉的棉纺厂家属院
在白银,也是同样地沉闷。在高家四口人租住了7年的棉纺厂小区,早已不耐烦的居民说“都来了二十几波记者啦。”然而又如何?他们都不知道那十几二十天现身小区一次的高承勇到底在哪些厂矿打散工。你所知道的是,他住的这个小区,距离他两桩相隔12年的杀人案点,各是东西距离500米左右。他住在这个小区,在永丰路上,东为1988年杀“小白鞋”的工农路,西为2000年杀罗姓女子的西山路......“这家伙心理素质超好,而且我发现他每次作案都喜欢在最后一个单元,或里面一排房子。”我跟老刘一个个踩点后,他这么兴奋地说。但你无法揣测,当这个双重人格、绝对冷静的杀手每次走经那些有他陈年旧事的街区,他作何想?

白银通往青城镇的黄河大桥,高承勇去作案和回家的必经之路,当年黄河上第一座吊索桥,近几年拆除后重新修建
老刘甚至用了戏剧性的说法,“这家伙每次来白银杀人,都好像度个假。”因为我们发现,他大多作案点,走走就能到,这个西北边陲的矿城犹如小小的迷宫花园,随便走着都似曾相识,或就接上了。我们还揣测过,他如何过来,用什么交通工具:如果是青城的那种“大轿子车”(公交车),就会停在一个叫“水川路十字”的街口;如果从他从内蒙打工回白银,无非就要坐到汽车站......但谁知道呢,如果他坐拖拉机或者骑车自行车从青城过来呢?无法获取核心信息的我们,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地攀缘上“受害人家属”这最后的稻草,于是铺天盖地的家属回访出现了,然而意义何在。

俯瞰白银市
这种情况下,如何去铺展一个杀手和一段“白银往事”?如何不从外因上去做粗暴的因果联系?这问题始终困扰我,当我住在那著名的也曾出现过强奸案的白银饭店的时候,心脏始终不能落地。这座城市在那几天的流传中俨然已给我一种蛾摩拉般罪城的印象,然而它再阴暗晦涩也无法给我一个合理的对杀人并肢解的解释。或许你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聆听那些人对他的印象,以及这座城市给予你的空间认识。我们始终要相信,一个狂魔般的人,也始终是一个拥有自己复杂的生活世界的人,他咫尺天涯般的秘密、他常人的性格、他无辜的家人......
就因为谁都无法穷尽另一个人,以至于我们要始终谨慎于主观代入一个人。其实凭借冷静和观察,已足以呈现白银,并不那么绝对地去呈现一个至今都面目模糊的高承勇。时间会让线索清晰或丰满,也许科学更能解释一切。
(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将推出一组白银案报道,杂志将于本周三面世,敬请关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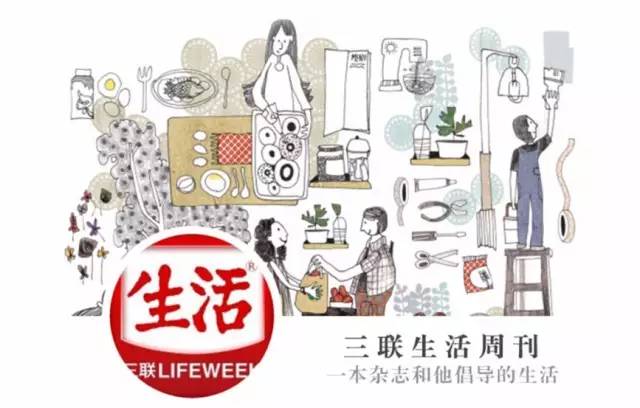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三联生活周刊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