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
2016/9/3 哲学园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领先全网 诚意推荐



长按二维码购买

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访谈录 张卜天 访谈整理 张卜天按: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是荷兰著名科学史家,专门研究科学革命。他生于1946年,早年在莱顿大学学习历史,1975-1982年任莱顿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Boerhaave)馆长,1982-2001年任特温特大学科学史教授,2006年12月起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科学史教授。其代表作有:《量化音乐:科学革命第一阶段的音乐科学》(Quantifying Music. The Science of Music at the FirstSt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80-1650,1984)、《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The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1994)、《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De herschepping van de wereld. Het ontstaan van de modernenatuurwetenschap verklaard,2007)、《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How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 CenturyBreakthrough,2010)等等。其中《世界的重新创造》和《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已由我译成中文。2012年8月,值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荷兰文学基金会与比利时文学基金会代表团访华之际,科恩教授来到北京。我有幸就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等话题对科恩教授作了采访。张卜天(以下简称张):科恩教授,您最早是学社会经济史的,后来为何会转向科学史特别是科学革命研究?在这一转行过程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科恩: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学生时,我主修社会经济史,但辅修科学史。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赞成议会民主,但仍然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世界。我想弄清楚该党派当时最大胆的一些思想家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界限的,以及他们采取了什么替代方案。
1974年我通过了答辩,并出版了博士论文。此时我意识到,我想回到一个曾经思考过的历史问题。最宽泛地讲,那就是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于(比如1820年以前)我的祖先的世界。这是一个机械化运动的世界、电力的世界、快速通信的世界等等,各种人可以得到各种商品。商品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对极少数精英是充足的,而是对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是充足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是这样,至少目前还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一直在跨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门槛。现代化正在迅速进行,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现代化进程最先开始于欧洲?我在指定给我们的教科书中遇到了这个问题,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没有一种回答能让我满意。原因是,当时(60年代)就这个问题进行写作的历史学家们似乎遗漏了在我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东西,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兴起对于现代世界的兴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现代科学,我们的现代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变得完全不可能——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技术。所以我开始怀疑,如果不能首先解释我们现代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欧洲最先出现,如何可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兴起这个著名的问题?正是由于现代世界的兴起,我们今天的生活才迥异于(大约)19世纪20年代我们祖先的生活。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成为一名专业的科学史家,而且主要兴趣集中在现代科学第一次产生的那个时期,即当时和现在所谓的“科学革命”。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
你问我最大的体会。回答很简单,但并不谦虚。我认为我已经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两年前出版的《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 Century Breakthrough)一书回答了我大约45年前学习历史时提出的问题。“使命完成了”——是不是一种美妙的体会?
张:您曾担任过7年布尔哈夫博物馆馆长。不知您对这段经历有何体会?得到了哪些收获?
科恩:从1975年至1982年,我担任了7年布尔哈夫博物馆(科学史国家博物馆)馆长。在这一时期,荷兰的博物馆发生了深刻变革。大家普遍认为,历史博物馆不应只为行家服务,而要使广大公众感兴趣。我的同事们是真正的策展人,他们每个人负责一类特定的收藏,比如物理收藏或医学收藏。我的工作是监督所有文本的制作,并与我的同事们一起重新规划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临时展览是1979年惠更斯诞辰350周年之际所举办的惠更斯展览。
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7年后我也很高兴有机会重返学术界。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有三个方面。我学会了为广大读者以非学术的风格写东西,同时并不牺牲内容的深度。我对惠更斯的工作——特别是他定量的音乐理论——了解了很多。当然,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科学的物质一面及其历史——科学仪器的历史为何对于科学史本身是不可或缺的。
张:您曾把“科学革命”概念称为“秘密宝藏”,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为何称它为“宝藏”,又为何称它为“秘密的”?
科恩:在我1994年出版的编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中,我曾把“科学革命”概念称为“秘密宝藏”。那时我的意思仅仅是说,科学史家们拥有一把不可或缺的万能钥匙(“科学革命”概念)来解决现代世界的兴起之谜。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一直在就此进行激烈争论,但这些学者未能充分注意我们这份隐藏得很好的宝藏。我周围的人正在迅速放弃任何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概念,而我们科学史家也在忙于掩埋它。
张:您在1984年出版了《量化音乐:科学革命第一阶段的音乐科学》(Quantifying Music. The Science of Music at the FirstSt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80-1650)一书,您为什么如此重视音乐对于科学革命的重要性?我知道您非常热爱音乐,音乐在您的生活中占据何种位置?
科恩:对于科学革命而言,与当时的任何其他领域相比,我并没有赋予定量的音乐理论以更大的内在重要性(在关于近代科学如何出现的叙事中,我认为关键角色无论如何不是各个学科,而是我所谓的“自然认识模式”[modes of nature-knowledge])。我在《量化音乐》中的观点其实是,历史学家相当一致地忽视了这个主题,而大多数主角(伽利略、开普勒、贝克曼、笛卡儿、梅森……)都为解决希腊人(始于毕达哥拉斯)留下的定量音乐理论中的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便如此,我研究这个主题当然是出于我对音乐的热爱。我是教堂管风琴的业余演奏者。莱顿的圣彼得教堂中有一架在荷兰数一数二的教堂管风琴,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幸弹奏它。当时我能够演奏不少作品,比如巴赫的F大调托卡塔与赋格,这是一首相当复杂的长曲,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一直经常听音乐,陪我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歌剧院看演出。即便如此,我还深深地记得一场京剧演出,但不是最近,也不是在北京,而是1978年在香港新界的一幢小棚子似的建筑里,当时也许有100人出席,除了我们4位荷兰游客,所有观众都是中国人。我对故事的主线、文化背景或音乐的五声音阶一无所知,但我仍然很享受那场演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并不认为我们总是需要“语境”(context)知识才能享受“文本”(text)。
张:您为何坚持认为科学革命概念不应取消?把创造性活动还原为社会方式的“新语境主义”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科恩:我之所以认为科学革命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原因有两个。它是可以用来解决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最先出现于欧洲这个问题的唯一概念。此外,我的确只在部分程度上赞同过去几十年针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即它已被过度使用,以致变得不再连贯。特别是,“数学化”是科学革命的关键这个已逾70年的想法已被证明无法把握科学革命,因为研究者们在此期间发现科学革命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我同意后者的批评,但不同意许多英语世界的科学史学得出的结论,即因此最好取消这个概念。我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彻底修改它。我所做的恰恰是在一种比迄今为止更深的层次上寻求连贯性,为最终获得一个多元化的、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留出所需的余地。事实上,我自认为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
至于“新语境主义”,我原则上认为它是对历史学家装备的重要丰富,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做真正的历史理解。确定某种想法或做法如何会出现在某时某地可能很有启发性。但我反对以还原的方式这样做。任何新事物都是局域出现的,如果某个主题能在其起源地之外被接受和加工,那么只考察当时起源地的情况从来也不会穷尽这个主题。任何有价值的想法总是会超越自己的起源,在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获得普遍价值(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一样,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阿姆斯特丹都有效)。
张:关于科学革命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您持“相对非连续”的立场,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种观点?
科恩:我现在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端由三次不同但却平行的“革命性转变”所组成。开普勒和伽利略用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数学处理取代了希腊人高度抽象的数学科学。贝克曼和笛卡尔用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由不断运动的物质微粒所构成。培根、吉尔伯特、哈维和范·赫尔蒙特按照达·芬奇、帕拉塞尔苏斯或维萨留斯的方式,把实用目的的精确观察变成了我所谓的“发现事实的实验”(fact-finding experimentation)。这些都是转变——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受到影响。历史上没有凭空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件是革命性的,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某种长期存在的样式内部发生了彻底断裂。即便如此,这三次转变并不具有同样的革命性——与第二次和(特别是)第一次革命性转变相比,第三次革命性转变有更大的连续性。
张:您是世界上极少数研究比较科学史的学者之一。您为什么认为比较研究对于目前的科学史如此重要?您认为在对不同文明做比较研究时,最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么?
科恩:在与我的一位荷兰同事交谈时,他曾把比较称为“历史思维的发动机”,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如果不把事物的实际过程与可能的过程进行比较,或者与其他地方足够类似的情况下的过程进行比较,那么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可行解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罕见的。需要避免的一大陷阱是没能深入思考把什么与什么相比较,以及在何种分析层面上进行比较。另一个陷阱是使比较完全由先入之见所主导,尤其是就跨文化比较而言,这种先入之见往往表现为一些未经反思的看法,如一种文明相对于另一种文明具有某种所谓的与生俱来的优势或劣势。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愿意如实地看待事物本身,而不是按照某种预设的模式设想它们应该表现成什么样子。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
张:相比前人,您关于科学革命的最新解释主要新在哪里?
科恩:我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包含了一个主要新颖之处:“革命性转变”概念本身,以及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端可以被卓有成效地分析成上述三次平行的革命性转变。
我还在我的最新著作中表明,在1660年左右三者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融合,到了1685年发生了最后一次革命性转变(牛顿的),因此我最终认为科学革命由六次密切相关、彼此连贯的革命性转变所构成。我试图解释每一次革命性转变。因此,我不再认同过去几十年通过某种无所不包的原因(印刷术、资本主义、清教主义等等)来解释科学革命的所有那些努力。
我还认为,现在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基础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具体做法我想我们接下来还会谈到。
张: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和《世界的重新创造》中提到,希腊自然认识至少经历了三次文化移植,请问文化移植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吗?中国自然认识的发展一定是“辉煌的死胡同”吗?这种“死胡同”是否特指无法发展出西方科学?仅仅拿钟表、罗盘等个别发明或发现做例子似乎有些单薄,中国的“发展潜力”难道只由这些东西来体现吗?
科恩:恐怕这里我必须处理好一些概念性的议题。在中国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其自然认识模式实际从未间断过,与之相比,最多持续一千年的古希腊自然认识模式就短得多,但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反差。在我看来,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希腊文明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两者都产生了大量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然认识著作,可以进行相互比较,或许能产生丰富的洞见。还请注意,我所谓的“实际上未曾间断”仅仅指中国传统。事实上,希腊传统中断了——与中国文明不同,希腊罗马文明的确走到了尽头。诚然,包含各自文明的这两大帝国都曾被外国侵略者侵占,但中国文明经历了蒙古族和满族的猛攻之后基本保持完好,而在大约公元400年到公元650年之间,希腊罗马文明却彻底灭亡了。
由这些基本历史事实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我称之为“文化移植”。我指的是整个知识体转移到一种以前没有接触过它的文明中。其核心思想是,移植到尚未涉足的土壤为被移植文献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得到新的更好的发展、扩充、丰富甚至是较为激进的转变。
在这方面,我的确利用了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关于“一个辉煌的死胡同”的想法。他提出这种想法是为了强调欧洲中世纪的机械钟与苏颂在数百年前制造的远为精确的水钟之间的巨大差异,机械钟虽然起初并不是很准确,但后来事实证明极为灵活,而水钟则被证明并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事后看来,一项发明或发现可能拥有一定的潜在发展潜力,这种潜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明显,而且仅在某些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我利用了这种想法,并把它从个别发明或发现拓展到古希腊或古代中国那样的整个知识体。不过,我用苏颂的水钟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潜在发展潜力”的观念。我对中国研究自然的进路(李约瑟称之为“有机唯物论”)是否包含这样一种发展潜力并没有固定的看法——我觉得有发展潜力的可能性不大,但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但我的要点是,即使它有发展潜力,也从未得到机会来显示。这里有我本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我称之为“文化移植”。如果不经历一系列“文化移植”,进入尚未涉足的其他文明,中国和希腊的自然认识模式都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转变。希腊的自然认识著作得到了三次这样的机会,它先后被移植到伊斯兰世界、中世纪的欧洲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约从公元800年到1000年,它被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大约从公元1100年到1200年,它被从阿拉伯文译成了拉丁文,大约从公元1450年到1600年,它被从希腊文译成了拉丁文。在每一种情况下,学者们都设法利用翻译过来的希腊自然认识著作,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加工它们。而中国的著作则一直基本保持不变,直到19世纪。当然我并不是说汉代的综合确立之后它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而只是说,较为彻底的革新一直没有机会显示出来,因为中国文明总能成功地教化蛮夷。在我看来,这样的机会(即文化移植的功绩)对于理解近代科学的出现的确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的新书中,我得出了以下结论:
事后看来,随着墨子文本谱系的逐渐消失,渗透在中国自然认识著作之中的有机的/关联的世界观可能会或者(更可能)不会有其希腊对应物所拥有的潜力,能够发生转变而导致明显的近代科学出现。在实际成就方面,无论是希腊著作还是中国著作都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包含在希腊而不是中国之内的潜在发展潜力有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
张:李约瑟用“百川归海”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这似乎是讨论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必要预设。您认同这种预设吗?您认为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或您所说的自然认识)是同一类型或服务于同一目的吗?(比如我认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科学或迷信)。席文和帕梅拉·朗(PamelaO. Long)等科学史家会质疑像李约瑟问题这样的追问是否有意义。正如朗所说,这就像追问“16世纪的法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儒家思想”一样荒谬。您为什么认为他们走得太过,而讨论李约瑟问题仍然有意义呢?
科恩:对于(大约)牛顿之前的自然研究进路,我认为不说科学,而说“自然认识模式”(modes of nature-knowledge)或其他一些包容性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例如,当你把亚里士多德称为“科学家”时,你几乎不可能不在心灵的某个偏僻角落把他想象成一个正在努力实现下一个突破的穿白制服的实验室工作者。如果依照传统把亚里士多德、道家或笛卡儿等人的观念称为“科学”,将会引起太多联想,它们反映的是当今科学,而不是任何据称早期的对应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李约瑟的“百川归海”比喻。一种文明中的发明可以相对容易地传播到旧世界的各个地方,但与技术不同,在追求自然认识的过程中,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在一种文明中获得的见解才能真的被另一种文明所采纳。炼金术和它的一些理论、“图西双轮”(Tusi couple)和其他少数几个例子在我看来是仅有的被充分证明的例子,而我们经常在通俗学术文献中碰到的其余的例子都是猜测或一厢情愿或两者兼而有之。
此外,正如我在回答你前面的问题时所指出的,我认为希腊和中国研究自然的进路是理解整个自然界的两种截然不同但却同样英勇的努力。每一种都应当就其本身去考察,就像席文和劳埃德在其《道与名》(The Way and the Word)一书中所做的那样。此外,正如我在前一回复中所指出的,希腊和中国的自然认识著作本身都不是近代科学,甚至也没有朝着它前进。这方面的唯一可行的区别我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历史变迁(某些完全不可预知的军事事件)给了希腊自然认识著作以中国从未有过的机会:在新的尚未涉足的文明中获得新的机会。至于其他,最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这两者进行独立考察。因此,关于如何最好地解释风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在我的编史学著作中详细讨论过席文对比较方法的反对意见。我并不同意这些意见,但我认为它们是严肃的,非常值得反驳。帕梅拉·朗的评论只是表明在科学史上关于比较的思想状况仍然很原始。我本人花了数天、数周和数月来思考将什么与什么相比较能够受益最多。什么文明、什么阶段的什么状况看起来足够相似,以使持续的大规模比较既可行,又能对大规模分析有潜在的益处?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对中国和希腊进行比较(特意不像李约瑟那样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另一个持续的比较也源于此,那就是我对伊斯兰自然认识的黄金时代(公元1050年左右)的数学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元1600年左右)数学科学所作的比较。思想状况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比鲁尼(al-Biruni)已经达到与晚得多的毛罗里科(Maurolyco)等人大致相同的水平,但结果完全不同(前者是急剧衰落,后者则是发生革命性转变)。为什么?
此外,帕梅拉·朗那个愚蠢的伪问题也体现了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缺乏足够的能力将近代科学与任何其他文化产物区别开来。儒家思想作为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明显与某种文化密切相关,而近代科学则有异乎寻常的能力来提出普遍有效的见解,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或进化论。导致帕梅拉·朗这样相当理智和有能力的科学史家的思想遭到如此破坏的正是你在前面问题中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张:对于您的这个回答,我并不完全赞同。我并不是说回答李约瑟问题完全没有意义,但我认为科学的确是依赖于文化的,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自然认识在类型和性质上也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从来也提不出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普遍化、形式化、对象化的东西。这也许是我们最深刻的分歧所在。不过关于这一点有太多可以谈,我们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您在书中还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科学认识的衰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我们今天已经习惯的科学的持续增长倒是一种“病态”的反常现象,并且指出,衰落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需要解释的是衰落在何时发生。如果像书中那样请您来做“趋势观察员”,您能否展望一下今天的科学发展会在何时衰落?
科恩:我必须重申“科学”与我所谓的“自然认识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一项重要区别在于,你所提到的“繁荣/衰落”的自然样式(它确实是传统自然认识发展的标志)自那以后已经被近代科学所取代。近代科学依赖于之前完全(也必然)不具备的两大支柱:(1)通过概念、理论和实验而获得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2)由于基于科学的技术,在整个社会中获得了牢固的基础,没有这种技术,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完全无法想象,实际上也无法忍受。我很看重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bubani)捍卫的一种观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将会转到亚洲,以至于回想起来,西方的中心地位仅仅持续了几百年时间。我并不认为他的整个论证都令人信服,但这一想法耐人寻味,当然也不乏某种现实性。然而,这与近代科学本身有可能像伊斯兰和欧洲中世纪的自然认识那样急剧衰落完全不同。近代科学的整体衰落只可能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发生:要么是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要么有巨大的灾难使我们已知的大部分文明走向终结。就目前而言,这些可能性还很牵强,我认为无须对此花费太多心思。
张:近代科学当时如何能够成功地幸存下来?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中将其归因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培养的和解精神以及“培根式意识形态”的兴起是否显得勉强?
科恩:也许你不知道,是我最先意识到近代科学的兴起问题实际上是两重问题。不仅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而且是:它如何能够成功地保持下去?因此,我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全新的。在我的新书中,我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从1645年到1660年近代科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从17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种源于陌生感和亵渎感的浓重怀疑气氛如何因为你所提到的两大功绩而消散。我自认为我的论点足够可靠,它能被足够多的经验事实支持。当然,细节上的反驳总是欢迎的。
张: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中提到西方自然认识传统在发生革命性转变之前有三种模式,即“雅典”、“亚历山大”和经验观察,其中雅典模式提出了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第一原理来说明整个世界的性质。亚历山大模式则表现为“抽象的-数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试图解释,而是用数和图形进行证明,与实在的联系不密切。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的,它注重精确的观察和实际应用,认为真理不能从理智中导出,而只能到精确的观察中去寻找,目的是实现某些实际的目标。接下来我想结合这三种自然认识模式提两个问题。
首先,“雅典”模式和“亚历山大”模式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比如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体现的数学自然观如何定位?毕达哥拉斯一方面是数学传统的先驱,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柏拉图学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和构成五元素的正立体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您举出的两位“亚历山大加”的贡献者——开普勒和伽利略,前者是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后者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相对抗。很难想象能够脱离“雅典”模式来单独讨论“亚历山大”模式的升级。科恩:你提出了非常启发思考的问题。我必须重申我所作的概念区分,它反映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首先,最好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战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也是一样)理解成是在尝试一些只是到后来才得以固定的主题。对中国而言,最终留下了一种广泛的世界观——席文称之为“汉代的综合”。对希腊而言,则发生了双重固定。一方面,某些前苏格拉底概念,比如无限、变化、数等等成为四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观的结晶点,这四种世界观都有一种非常严格的概念结构——我为其保留了“自然哲学”这个概念。无论是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伊壁鸠鲁的还是斯多亚派的,所有自然哲思的基础都是用第一原理来推理,这种推理方式赋予了这四种世界观以更大的一致性,但与“汉代的综合”相比,也赋予了它们不太灵活的概念构造。此外,对于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经验现象是中性的,它总是要符合自然哲学的第一原理(这是与“汉代的综合”的另一大差异)。在亚历山大的自然认识模式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同样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某些观念,尤其是数的观念,但方式与雅典的自然哲学学派相当不同。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毕达哥拉斯最先发现的弦的振动所显示出来的数的规律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把这些规律性变成了一种全面的自然哲学的基石,而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则仅把它们用于计算,这对于现实世界的结构没有任何意义。
你说开普勒的灵感来自于毕达哥拉斯的观念和柏拉图对它的利用,这当然是对的。我并不否认,“雅典的”自然哲学与“亚历山大的”数学科学之间有某种关联。然而,开普勒与伽利略同时带来并作为后者补充的革命性转变是在“亚历山大的”数学科学中,而不是在“雅典的”自然哲学中。伽利略对自然哲学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立场来自托勒密,纯粹是讲求实际的或机会主义的(“挑选看起来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笛卡儿那样试图在某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使之协调一致。
张:对于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而言,您认为欧洲所从事的自然认识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欧所特有的一种外向型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但这样一来,一些更深层的观念演变似乎被忽视了。您一定知道,基督教所带来的不仅是实用,比如基督教的创世观对于自然观念的转变和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不仅仅是实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
科恩:我当然深知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的这种关联。显然,近代科学出现在一种基督教的气氛中,但我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那种气氛对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的情况下,我才的确看到了一种直接的基督教影响,这种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确实很难想象。当然,基督教本身远远不只是以实践为导向,只是我没有看到所有其他方面对于近代科学的兴起造成了什么决定性的差异。
张:如果说“雅典”和“亚历山大”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自然认识模式,那么难道中国古代就只有一种自然认识模式吗?既然西方传统内部能够细分成三条脉络,那么中国传统内部又如何呢?难道汉代的综合之后真的就铁板一块了吗?魏晋博物学、魏晋玄学、佛学的引入、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百科全书风潮……中国的学术模式其实一直在发生变革,只是站在西方的视角来看,觉得差异不大,但如果我们笼统地看待整个西方,而在中国传统内部细细分辨的话,应该也能区分出很多自然认识形式和多次变革和融合吧?
科恩:你关于中国自然认识的历史知道的肯定比我多得多。我仍在翘首企盼某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能够用英语或我可以阅读的其他语言出版一部权威的“中国自然认识概述”。即便如此,我知道你提到的一些发展。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视角的问题。你所提到的发展在我看来像是单一主题(“汉代的综合”)的种种变式,而不像希腊的努力所产生的两个主题(“雅典”、“亚历山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增加了一个。是否可以正确地说,久而久之,“汉代的综合”的所有这些发展的基本成分,尤其是道、气、阴阳、五行,又以更加微妙的方式经历了其他更基本的变化?在希腊的情况下,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智主义推理方式:一种是全面的/思辨性的/解释性的,另一种则是数学的/零碎的/描述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增加了完全不同的第三种,它主要是带有实用倾向的、经验主义的。而在“汉代的综合”以及千百年来对它的利用中,我看到的却是一种带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关联式的研究进路。所以我目前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研究进路是一个整体,当然肯定不是没有变化和重要完善,但并没有像希腊的情况那样分裂。
最后,感谢你提供这个很好的机会,使我能够澄清我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想法。我希望中国还有不少人能像你我一样,认为这其中涉及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阅读 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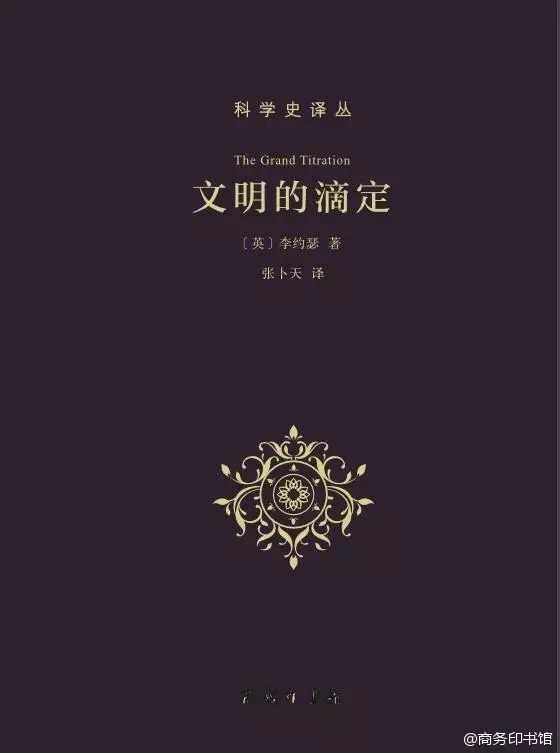

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